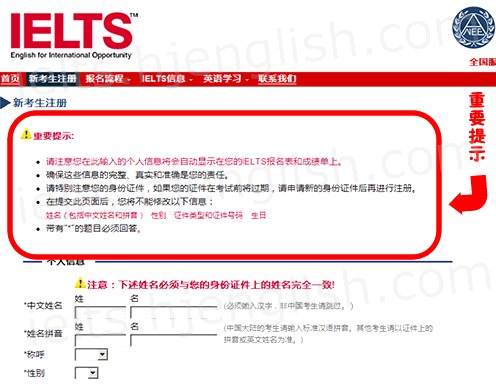2020 年第一季度,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蔓延,让正在不断被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所侵蚀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变得更加不确定。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一国产业或企业对经营活动所需外部资源的高度依赖,将导致其在利益相关者压力下的稳定状态遭到破坏,继而导致系统不稳定的风险状态,即为产业(企业)脆弱性。
中国制造业具有国际市场占有率体量大、高度嵌入全球价值链( Value Chain),但“两端在外”的特点。
一方面,中美科技领域的“局部脱钩”正在展开,打压以华为、中兴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民族企业依旧是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另一方面,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基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而形成的产业竞争力,将受到要素成本和单边主义的影响,可能出现过早、过快弱化的“早产”性质,而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力则在持续增强。
因此,全球经贸格局的加速动荡必然导致中国制造业基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布局以及源于生产要素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竞争力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继而呈现风险状态。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围绕中国制造业所包含的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两大类微观主体,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界定为一个特定产业内外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统计上显著地高于民族企业的一种风险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全球经贸格局动荡所导致的供应链断裂的隐患,将影响高度依赖全球价值链上下游的在华外资企业运营的稳定性,继而影响“连锁全球化”( )下中国在该产业上国际竞争力的可持续性。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了解:面对不确定的全球经贸格局,中国制造业尤其是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否足够强大?是否存在脆弱性?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又主要体现在哪个环节?其原因何在?
解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构建基于微观主体(企业)的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测度体系,继而判断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是否足够稳固以应对冲击,这也将有助于民族企业进行客观而清晰的定位,更有针对性地发现短板,继而提出能够在保持中国制造业“基础性地位”的同时,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对策。
基于国际分工的最新特点,本研究尝试厘清企业“国籍”所引致的“国家−产业−企业”不同主体之间经济活动的关联以及如何影响一国产业中不同层次国际竞争力的机理,在“产业国家”和“民族企业”二维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企业参与国际分工时竞争力的“实质−表现−结果”三个层次,创新性地构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二维度−三层次”测度体系,并以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本研究对2000至2013年中国制造业84482家企业进行量化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既不像宏观经济数字上表现得如此强大,也不像惯性思维所认定的那样只是基于廉价劳动成本等传统比较优势而(在面对全球经贸格局动荡时)表现脆弱,而是建立在其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分工并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符的国家特定优势和企业特定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特有的“中国制造”竞争优势。
其次,“外强民弱”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高技术产业中竞争力的实质和表现层次上。
第三,中低技术产业中的竞争力实质与结果层次呈现稳固性,但高技术产业在该层次的竞争力存在潜在风险。较高的生产率是中国传统制造业面对生产要素成本上涨、逆全球化趋势蔓延而仍然能够吸引大量外资流入的原因;同时,民族企业对国内资源依赖程度更高,对全球经贸格局的动荡具有更强的应对能力,但需要防范高技术产业核心技术的对外依存所存在的产业链断裂隐患。
第四,中国制造业上游度水平的提升、国外跨国公司所属母公司对研发环节和营销环节的控制及其对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优势,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局部脆弱性的主要原因。
(本文原题:“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新测度与解读——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深层次透视”。原载《财经研究》2020年第8期,作者余佩、蔡正芳、刘林青。)
外商从中国撤资的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打一大,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3年的22. 6亿美元攀升至2019年的1381. 4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从1997年的23. 6万家上升至2018年的59. 3万家。不少研究都指出,外资流入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在外资引进规模不断上升的同时,撤资现象也开始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除了媒体报道的一些案例外,我们也可以借助宏观数据粗略地估算撤资的规模。由于公开的统计资料缺乏与此相关的直接信息,我们采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差额”的借方金额对外商撤资的规模进行了大致的估计。结果显示,外商撤资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且2013年和2014年增速超过70%。我们还利用每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与外商投资企业年末登记注册数,估算了每年撤资的外商企业数量。结果显示,在2005至2007年,每年撤资的外商企业数口在2. 6万家左右,占当年新增外商企业数的60% -70% 。
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规模呈逐年下降的态势,2018年外商投资单位城镇就业人数较2013年缩减超过20 %,外商撤资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关注。
本研究基于1998 至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大样本微观数据,通过对企业经营绩效、生产率水平、出口行为等个体性因素以及企业所处地区和行业等环境性因素的分析,考察了影响外商企业撤资的主要因素。
研究发现:在企业层面,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盈利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参与出口的行为显著地降低了外商撤资可能性。由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的冲突,相较于绿地投资,并购型外商企业更易撤资;在地区层面,工资增速的上升会提高外商撤资的可能性。
针对港澳台和外国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密集度的提升更大地降低了前者的撤资可能性,而提高盈利能力则更大地降低了后者的撤资可能性。针对独资和非独资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和盈利能力的提高以及出口行为,可以更大地降低前者的撤资可能性,而地区工资增速的提高会更大地提升后者的撤资可能性。从撤资方式来看,提升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盈利能力和TFP(全要素生产率)等,可以更大程度地降低解散形式撤资的可能性,而以并购方式进入的外商以股权出售方式撤资的可能性更大。
(本文原题:“外商撤资的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原载《世界经济》2020年第8期,作者罗长远、司春晓。)
美国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实体经济

本研究选取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二季度作为研究样本区间,从总量和细分角度经验分析了美国财政政策变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动态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美国财政支出变化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动态特征。美国财政支出增加,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前对中国实体投资、产出和物价具有显著的长期刺激效应,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通过汇率渠道使中国经常账户受损对实体经济产生递增的负向溢出效应。在经济萧条时期,美国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较强。在经济新常态时期,美国财政支出通过利率渠道、汇率渠道和财政政策乘数效应渠道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的溢出效应均较弱。
其次,美国财政收入变化在 1998至2007年间对中国实际产出和物价的影响作用较弱,但对中国实体消费和实体投资具有递增的负向溢出效应。即美国减税会显著刺激中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2007年后美国减税不仅会对中国实体投资产生越来越强的正向溢出效应,且显著促进中国实际产出增长。尤其是在2012年之后,美国经济增长逐渐恢复,此时美国减税会明显增强民间对未来短期实际利率下降 的预期,通过国际资产价格渠道显著降低利率刺激中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且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减税的财政政策乘数效应越来越显著,汇率渠道的负向溢出效应较弱,导致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促进效应 越来越强。
第三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造业的优势,美国在2005年之前扩大财政赤字对中国实体投资、实体消费和物价分别具有递增、平滑和递减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对中国实际产出的整体影响较弱。2005年之后对中国实体投资和实际产出具有越来越强的正向刺激作用,对中国实体消费具有递增的中长期刺激效应。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减税方案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缩减了财政赤字率,会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财政赤字率每降低1%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分别引起中国实体投资下降0.0244%、0.0258%和0.0355%,并导致中国实际产出下降0.0057%、0.0118%和 0.0131% 。
第四,从细分角度来看,相较于美国利息支出,美国转移支付和消费性支出变化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更为显著。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转移支付每削减1%,在短期、中期及长期内分别会引起中国实体投资下降0.0218%、0.0245%和0.0266%,实体消费下降0.0249%、0.0183%和0.0059%。而政府行政管理和国防军费等消费性支出每增长1%,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分别引起中国实体投资增长0.0131%、0.0186%和0.0292%,且在中长期内分别带来中国实体消费和实际产出1%的提升。特朗普执政时期企业所得税、生产与进口税每降低1%会给中国实体投资带来0.015%~0.03%的提升,且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这种溢出效应也非常明显。
美国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及其传导渠道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当人民币汇率制度为单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时,美国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利率渠道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溢出效应。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通过汇率渠道产生的溢出效应逐渐凸显,且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处于严重萧条状态,此时美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的溢出效应较强。此时,中国也采取了如4万亿投资计划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美国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了加强中美两国财政合作的必要性。
(本文原题:“美国财政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原载《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作者吴安兵、黄寰、张燕燕。)
正确评价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
稳就业是“六稳”政策之首,对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意义重大。在中国实施主动扩大进口和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双重背景下,本研究基于 2000至2013 年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研究发现:从总体来看,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增长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且这一影响主要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企业价格加成两个渠道发挥作用;从上下游关联行业视角来看,上游行业进口竞争对企业就业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下游行业进口竞争对企业就业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从行业层面来看,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行业总体就业影响不显著,但是会导致就业在企业之间流动,就业主要从大企业、高生产率企业、高人力资本企业和国有企业流出;来自美国的消费品进口竞争和资本品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间品进口竞争对企业的就业增长无显著影响。
总的来看,来自美国的进口冲击,虽然对中国的总体就业没有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会导致国有企业就业下降、就业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流动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
(本文原题:“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就业”。原载《财经研究》2020年第8期,作者魏浩、连慧君。)